是因为学术。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正在做的研究也是和劳动紧密关联的。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些没办法理解的问题,无人可问,问了也将信将疑,非得要踩到那片泥土,亲眼见到才心里踏实。
二是出于“情怀”。扶贫是我关心的问题。2016年暑假我随北大的考察团到甘肃考察扶贫情况。甘肃的调研经历让我在现实世界有了一个研究的抓手,但是我始终担心会把一个局部的现象当成全局的共性,成了摸象的盲人。西南地区是扶贫的另一个重点,而我从来就没来过这里。如果能将四川和甘肃的扶贫情况两相对照,就应该能更全面地了解扶贫的真实情况。导师姚洋教授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让我能够暂时放下在北大的科研工作,参与到一段充满未知的旅途。
调研的第一站是偏远的马边县沙腔乡。由于公路还没有硬化,从县城到沙腔乡需要两到三个小时,而且沿路极其颠簸。到了沙腔乡,我们受到了当地和阿虎书记的热情接待。是彝族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很看重教育。江堡书记是少数当地的大学生,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后来调回家乡工作。阿虎书记早年在外打拼,攒了一些积蓄后回到家乡工作。我们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在北京学习生活了快六年的“城里人”,沙腔乡的经济条件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当我们被江堡书记带着走进一家小卖部的地下室,得知这里就是未来三天我们留宿的地方,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之前的情怀志趣荡然无存,唯一支撑我留下来的就是身边的同伴们。
刚把行李放下,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第一个调研地点:二坪村。乘车途中迎面走来几位中年彝族男子,穿着和城里的年轻人无异,只是手中拿着一些奇异的道具,边走边跳边唱和。我们问司机师傅这是在做什么。司机师傅哈哈一笑:“这是在做迷信嘛!”我想起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里对彝族的毕摩文化的描写。所谓毕摩,“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彝族的祭司。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认为毕摩文化是一种迷信,禁止相关活动。但是彝族同胞还是在婚丧嫁娶和有病的时候请毕摩偷偷做法事。有意思的是,虽然心中仍然信仰毕摩,彝族同胞们也随着汉人把宗教活动称作“做迷信”。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有了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传说中的祭司穿着牛仔裤、皮夹克做法事,村民明知这是“迷信”还要花重金来做。但是转念一想,我们汉人不也保留了很多民间宗教仪式吗?我们明知道先人已去,还是要在清明节烧香献礼,祭拜先人;我们早就不相信过年的传说,还是要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贴对联,贴福字。按照简单的理性人假设,这些行为似乎是不理性的,但是从一个族群的角度看,这些“迷信”恰恰在凝聚族群、寄托情感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知拐了多少弯,我们到了山间的二坪村村委会,也就是我们第一天访问的地点。这次访问是在一片“手忙脚乱”中进行的。访员们才和村民聊上一两句,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里上了年纪的彝族同胞根本不会汉语,而很多会汉语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还好有村长、村支书和一些志愿帮忙的年轻人,我们才得能继续开展工作。
令我们欣喜的是,彝族同胞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一方面原因是访问有一定补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地的民风淳朴。我们的午饭是在村小学的乒乓球桌上吃的。当时小学正好下课,看见我们这些陌生人,小学的孩子们既好奇又不敢接近,就远远地看着我们吃饭。几位女同学把我们在县城准备的饼干、面包分给孩子们,瞬间所有小学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聚到了我们身边,排着长队领饼干。有的孩子手里拿着一块又来排队领,我们也不忍心拒绝。后来可能是小学的老师批评了他们,孩子们回到了教室。我们给他们饼干,他们也不要了。看着他们简朴的衣着、黑红的小脸、清澈的双眼,我不禁暗暗担忧孩子们的未来。在调研中我们得知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小学毕业的村民也不会汉话。教育是地区和个人发展的根本,但是教育投资恰恰又是见效最慢、短期收益最低的。如果眼前这群孩子仍然接受不了好的教育,他们很可能还要重蹈先辈的覆辙。
吃晚饭的时候已经是七八点钟了。小饭馆虽然简陋但是菜品不错,每道菜一上桌就被大家风卷残云地瓜分光了。我比较爱喝饮料,自己点了瓶可乐。发现饮料瓶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可见这里的饭馆顾客有限,即使有顾客,愿意消费饮料的也不多。这一点在访问中也得到印证,村民基本是自给自足,自己吃自己种的粮食,持有现金很少,消费和购买都不多。
晚饭之后大家都挤到乡政府不到十平米的办公室蹭wifi,我们三个督导汇总材料,访员们上传数据,还有同学忙着改论文、写作业。一阵忙碌之后,我们回到宾馆准备休息。男生们(比如我)连脸都懒得洗,用手机打了几局游戏就和衣而卧,很快就鼾声如雷。女生们陆续到唯一一个有灯有热水的卫生间洗漱。这是个神奇的卫生间:它的门能轻易锁上,但是很难打开,以至于几乎每一位同学都有被锁在卫生间和帮别人逃离卫生间的经历。最惊险的一次是旅馆老板娘拿着菜刀把卫生间的门撬开(我不禁联想到“围城”的隐喻: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在这种条件下,一部分女生还能坚持每天洗澡,必须得说是一个奇迹。
第二天的工作是在一片“诗情画意”中开始的。我们乘车来到河畔,一座木桥连接着此岸与彼岸的竹林,远处是葱茏的青山,云雾缭绕。大家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照相,发社交平台,搞得当地村民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家门前这山这水如何让这群“上面”派来的大学生如痴如醉。在村民和干部们的配合下,上午的访谈比较顺利,中午我们转移到山上的村委会进行访谈。沿着盘山路上行,我们正真看到了背着娃娃赶山羊的妇人,看到了伫立在农田中看着爹妈劳作的孩子。生活,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同过去的几百年一样。我们在当地人脸上时常看到一种久违的质朴的微笑。
来到到山顶,一片精致的二层住宅吸引了我们。不用问,这一定是政府建造的异地扶贫搬迁房屋。眼前的景色不禁让我们感慨政府的扶贫力度之大,我们没想到的是地方干部为扶贫付出了多少心血。
下午的访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位彝族大伯一直在为我们当翻译,和书记一起帮我们联系受访村民。我们渴了,他就给我们从亲戚开的小卖部拿水,分文不取。一位访员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水杯,水撒了彝族大伯一身,他没有顾及自己,下意识地先保护我们访问用的平板电脑不被打湿。不知道是因为外表还是情感,我后来感觉这位大伯特别像焦裕禄。下午的插曲是一个醉汉。同学们入户访问时,他出去喝酒了,他的妻子接受了访问。后来他回家得知这件事,也许认为自己失了面子,就追到村委会来要求我们重新访问。被拒绝后,他火冒三丈,大吵大闹,被阿虎书记和几位彝族汉子架着赶走了。我们临走时,彝族大伯特意来和我们握手,替醉汉道歉。“你们来我们山里不容易,”大伯说,“我们是主,你们是客。要是刚才那个人再闹,我第一个去教训他。”
第二天的工作结束了,回来的路上,我和一位川大的同学聊一些学术问题。被我们的话题吸引,也加入了讨论。我万万没想到,阅读甚广,对经济、政治、历史都很了解,而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快到驻地时,江堡书记告诉我们,晚上他要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乡政府对面的小饭馆。饭馆并不大,四五张桌子并到了一起。和阿虎书记带着其他几位彝族、汉族的地方干部一起唱了彝族的“祝酒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虽然听不懂彝语,但是歌曲中的情意我们完完全全感受到了。晚饭除了平时的菜品,又增加了当地特色的鸡汤等土特产。阿虎书记坐在我旁边,和我聊了很多当地的情况和基层工作的艰辛。比如,白天我们在山顶看到的异地扶贫搬迁房屋,在建设前需要从村民那里征地,阿虎书记自己去做工作,找家族的人去劝说,最后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一定给征地村民足额补偿。但是地征上来了,房子建起来了,上级政府的拨款却迟迟没有下来。村民们纷纷怀疑是他把补偿款贪污了,他很委屈,也很为难。又比如,他谈到当地婚丧嫁娶送礼的风气,举了自己家的例子。十几年前母亲生日,远近的亲戚牵来了三十九头牛。按照当地的风俗,这些牛必须全部杀掉。阿虎书记当时还没有在政府工作,但是见过世面,劝说父亲只杀九头,分给亲戚吃掉,剩下的三十头牛卖掉。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如果他敢卖牛,就不认他这个儿子。后来在县里工作的亲戚的劝说下,阿虎书记还是把牛卖了二十二万元,留给家里老人作为养老金。我问阿虎书记,送礼有这么重要吗?他说,重要。如果送的少,不仅自己家被人瞧不起,整个家支(彝族对于家族的称呼)都会被瞧不起很久。每逢聚会赶集,其他家支的人就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阿虎书记早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乡里组织村民立下乡约,限制婚丧嫁娶的送礼额度,有了一些成效。谈到未来扶贫的方向,阿虎书记说,单纯地救济不是长久之计,根本上还是要“思想扶贫”,提高村民脱贫的意愿,配合政府工作。不知不觉我们已聊到了凌晨一点,由于第二天还有工作,我们不得已回去休息。躺在床上,简单准备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已经快两点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脑中都是阿虎书记刚才江的话。面对和阿虎书记这样的年轻地方干部,我不禁联想到《人民的名义》里的李达康。他们不是圣人,也有家庭,也有情感,也会有私心,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在基层默默工作,承受着上下的压力,维护着基层的稳定,谋求着百姓的安康。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的山路,泥泞的归途,让我感觉,这片山村与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远。而短短三天的时间,又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是和他们那么的近。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关与无关,仅是一念之间。在山外的世界,你读到他们、听说他们,也许会沉吟良久,然后继续生活,就像看过一片天边的云,什么都未曾发生。而来到了这里,你就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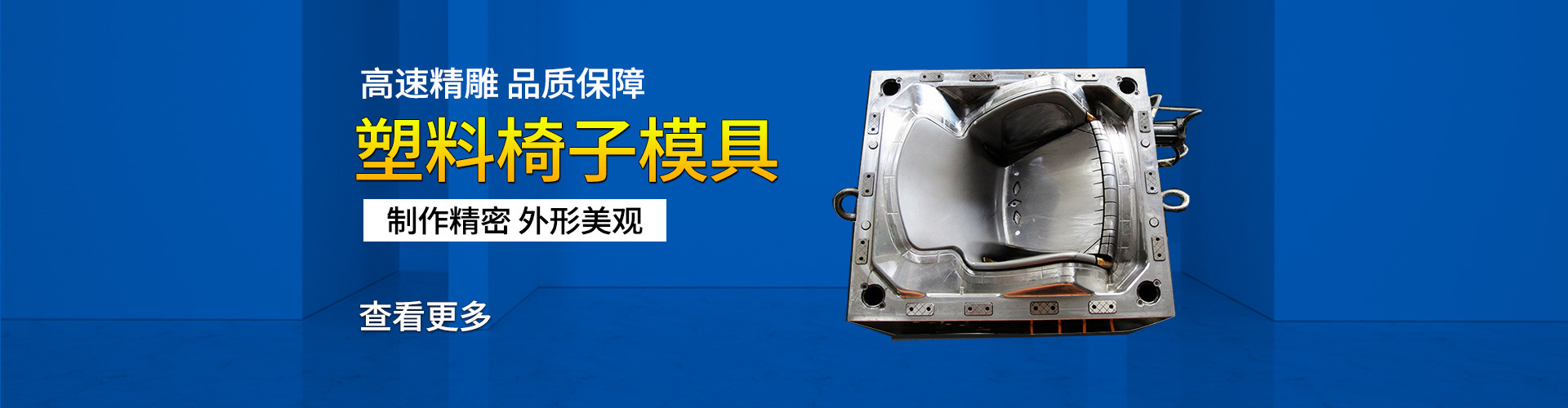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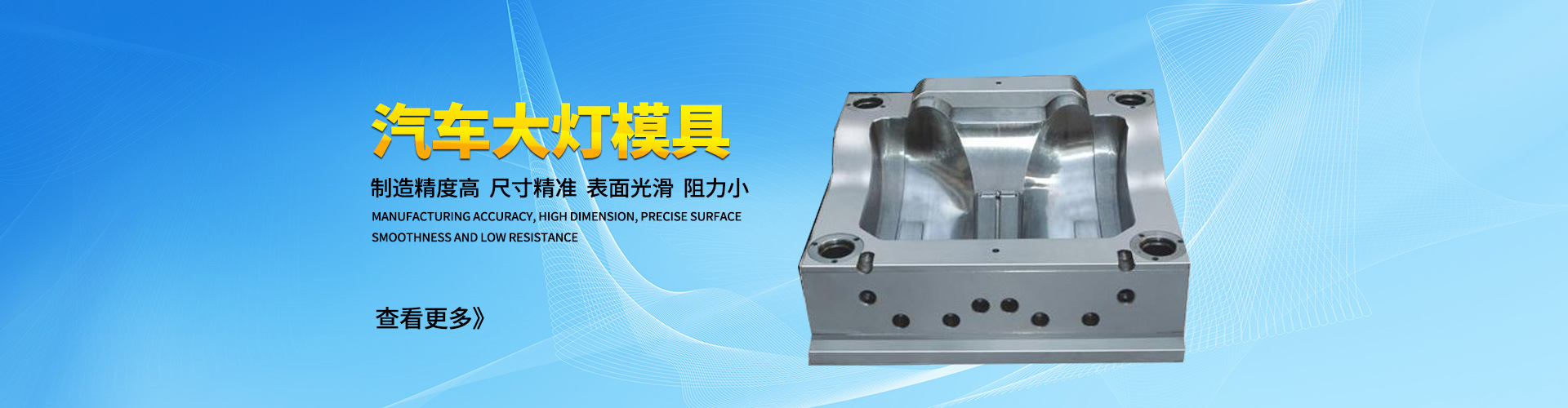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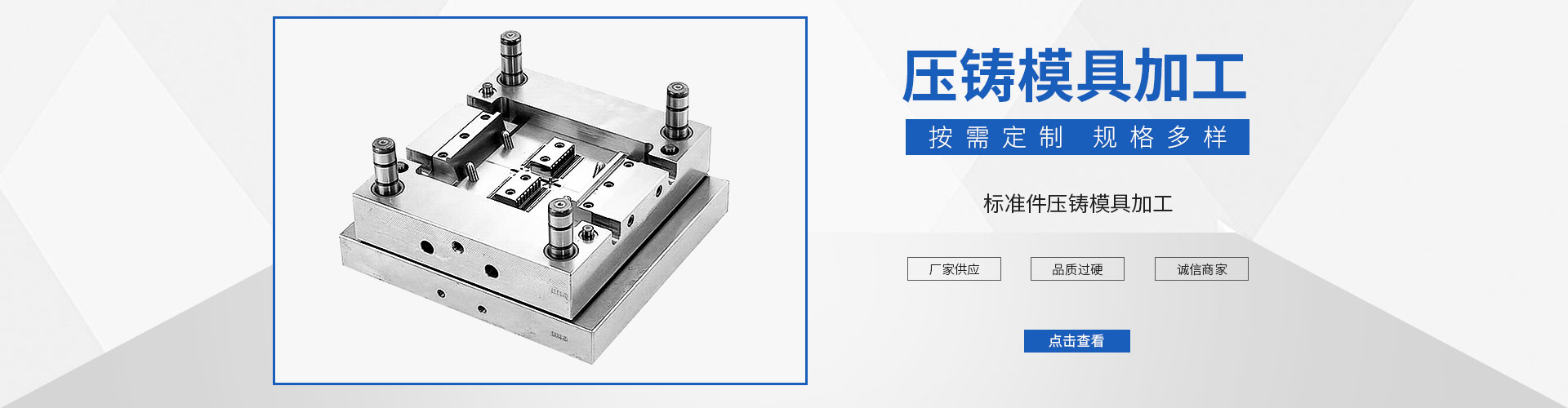
 更新时间:2024-02-28 16:08:33 来源:
更新时间:2024-02-28 16:08:33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