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彝族丧葬仪式由“崇生”意识、利益诉求、伦理道德、秩序重建及多重情感与原始观念等元素构成。它们分别形成仪式的本源性动力、监督性动力、呈现性动力等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彝族丧葬仪式的动力机制中本源性动力是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核心动力,呈现性动力主要起着一种表达和牵引的力量,而监督性动力则为仪式的举行划定着界限。正是如此有序的动力机制下,彝族丧葬仪式才得以成功举行,且确保了仪式的核心功能——救赎的达成。
彝族丧葬仪式既是彝族文化的贮存器,又是彝族社会重要的制度与规范。它承载着彝族的生命意识与生死观念。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意味着部分彝族生命的救赎、血缘关系的新一轮凝结与集体情感的重新确证,表征着彝区局部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目前,关于彝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之于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动力元素、运行机理及其核心功能的研究仍存在不足,而对此的精准理解与把握,之于我们理解彝文化,尤其是彝族丧葬文化,无疑是一把秘钥。丧葬仪式所表征的生死文化是一文化体区别于另一文化体较为独特、鲜明之处。因此,对于彝族丧葬文化的理解有助于理解彝文化的独特性。且之于彝族丧葬仪式动力机制的研究之于其他民族丧葬仪式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马学良在《㑩民的祭礼研究》一文中指出:“死后作祭,乃人类追祭死者之表示。”[1]但未就此展开。朱冬认为,云南少数民族丧葬仪礼的思想根源是“灵魂不死”观念[2]。黄龙光认为彝族关于死亡的想象即是彝族丧葬仪式起始的阐释[3]。
郝彧等研究认为凉山彝族葬礼是家支、邻里和姻亲等社会网络关系再整合的过程[4]。余舒研究认为,通过丧葬仪式的展演,实现和构建了人与大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生态人文空间[5]。穆春林研究认为,彝族丧葬文化承载着溯源、教化、调适、认同和内聚等功能,并认为其作为一种观念性文化,它与彝族历史共生繁衍,并在意识领域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6]。樊秀丽研究认为彝族丧葬仪式教育生者要学会面对死亡,直面人生[7]。单江秀提出丧葬过程是汲取力量,重建社会秩序,开始新的结构性的生产生活的活动[8]。
可见,尽管有研究者已触及到彝族丧葬仪式的部分动力元素,但尚未深入,亦未能全面系统研究其运行机理。现有研究对彝族丧葬仪式救赎功能的关注亦不足。我们以为彝族丧葬礼仪所实现和达成的各种功能都奠基于救赎功能,尽管此救赎功能更多是践行仪式时通过想象性的心理安慰而达成。
构成彝族丧葬仪式动力机制的要素包括:丧葬仪式的源生力——“崇生”意识、需求的内驱力——利益诉求、规制的强制力——伦理秩序、礼化的表现力——多重情感、观念的延续力——多重观念等。每一要素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着丧葬仪式的进行,并成为丧葬仪式举行的着力点。
彝族丧葬仪式历经千年变迁,一些仪式的具体形式业已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主体仪式和仪式的主体内涵仍保留,且尽管举办丧葬仪式花销较大,但直至今天,彝族认为不能取消此项活动[4],这便足以证明彝族丧葬仪式本身就具有一股源生力量——“崇生”。
“崇生”的核心意涵主要指对生命①、生活与生命力的崇敬。对生命的崇敬,其核心指向对人整个生命过程的关注,如对生命根源的追踪、对生命存在的养育、对生命安全的护持、对生命价值的实现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等。对生活的崇敬,其核心意涵主要指涉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美。彝族日常生活之美是一种在生活情境中对生存性行为和生活所用之物的非对象性的以实用性为基础的审美活动[9]。彝族对生活的崇敬,是其对生命力崇敬的基础、保证及其外在表现。对生命力的崇敬主要指对个体与族群生命之力的肯定与高扬。对个体生命力的崇敬,其最初意涵在对其大美——生殖之元的肯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文化交流交往的加强,彝族对生命力的高扬又拓展出与儒家“三不朽”相类似的向度。彝族对族群生命力的高扬,鲜明地体现在彝文古籍《指路经》当中。一定意义上而言,一部彝文古籍《指路经》就是彝族一个支系或宗族家族的迁徙史与生存史。《指路经》清晰地记载了彝族迁徙历程与生存之艰,但彝族坚强地生存并不断繁衍生息,展示了彝族族群生命之力的绵延不绝。
2015年12月,银隆完成第二轮融资,总额16.9亿元。2016年底,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格力”)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以个人身份入股银隆,并为其带来了万达、京东等“明星股东”,银隆第三轮融资共计30亿元。自此,这家尚未上市的新能源企业备受外界关注。
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动力与实践源泉。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实践活动。其得以举行的主体内驱力主要基于生死两安之下两界的利益诉求。生死两安意识是彝族“两个世界”——祖界与现世观念的想象性结果。生死两安呈现出的利益的物质化形态即福、禄、寿等。其对福、禄、寿等实际利益的向往亦存在两个向度——祖界与现世。在彝族看来祖界与现世之间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两个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世生者的福、禄、寿等实际、具体和可感的现实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祖界居住的祖灵。因此,生者不遗余力地举行丧葬仪式,将亡者送往祖界。如因当时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则后续也需弥补此仪式[10]。
亡者在祖界一如生者在现世一样生产生活。因此,生者需提供亡者在祖界生产生活一应所需,这种供给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实现:一是通过丧葬仪式的献牲仪式来实现,另一种则通过彝族毕摩念诵彝文古籍《指路经》等经文来实现。彝文古籍《指路经》详细告知亡者在祖界所需的住房、土地、水塘、牛羊等生产生活资料,这种告知主要是根据彝族毕摩通过神圣性的语词为其指定,并教授其饲养牲畜之法等生产劳作技巧。同时,毕摩还告诫亡者,其在祖界应继续保持勤劳致富的理念。只有确保亡者在祖界生产生活资料充裕、生活幸福美满,亡者才能为现世之人带来福、禄、寿等利益。同理,只有现世生者将亡者所需安排妥帖,亡者才会保佑生者。可见生者与亡者之间具有互惠性,因此相互之间关系紧密,无法分割。
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重建的强制。社会作为强大的集体,其运行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伦理道德就是这里面之一。伦理和道德都是群居生活中人们所一定要遵循的规则和习惯,以及由这种遵循所形成的德性或品质[11],即群体价值观念的标准化,也即文化的公共化。如果我们将人从其生存的文化语境,如语言、科学、艺术和道德信仰中抽离出来,则会沦为动物,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只有在个体之中才能存在和生存。倘若个体心灵和信仰中的社会观念消逝殆尽的话,群体的传统和宏图就不会被个体感受到,不会为个体所分享,社会也就“寿终正寝”[12]475。这即是社会力量何以要求必须举行丧葬仪式的目的。
传统伦理道德对个体的约束,以及个体的社会反应,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前进。当然,谁也没办法保证社会不会有暂时性的局部失序,如由一个亡者所引发的生活变故。亡者的出现就预示着其与社会的中断和集体力量的减弱。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局部性失序。这种失序还在于人们暂时无法对亡者进行秩序分类,亡者此时作为阈限实体,既不属于此地也不属于彼地,而是在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13]。因此,它处于阈限时期。
丧礼是对亡者进行分类的主要手段,丧礼被认为是不祥之物,与死尸的接触乃被认为不洁而危险[14]。因为不洁,所以它们极可能引发异常,对异常的认知会导致焦虑,并由此产生抑制和逃避。但人们紧接着就会寻找一个更具活力的组织原则,以便使污染象征所揭示的复杂的宇宙恢复平衡[15]。因为社会是无法容忍此种异常与失序长期持续下去。因此,它将动员并强制各种力量重建社会秩序,以使社会走向正常的运转轨道。仪式是失序回归、秩序重构的良方[16]。随着丧葬仪式的圆满完成,家族群体通过该仪式重获信心,情感得到满足,亲缘关系取得重建,于是他们重新安定下来,并相继恢复日常生活。
丧葬仪式的举行,是人性情感礼化的具体呈现。冯友兰指出,人的头脑有智性作用、感情作用,从智性角度讲,人确信人死不能复生,亦无法证明灵魂永生不灭,于此就没有举行葬礼的必要,但人同时具有感情的作用,人出于感情需要,希望亲人亡者能够再生,能够有一个魂灵在另一世界继续生存,这是丧礼举行的情感需要[17]。
人之于亲人亡者的情感极其复杂,刚逝去的亡者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是怜悯、恐惧、尊敬以及复杂多样的情感的对象。”[18]344 这些情感都需要被表达,表达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丧葬仪式是其中之一。“葬仪向我们揭示了与这些情感密切联系着的集体表象。”[18]344-345 可见,丧葬仪式成为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可视化形式。对此程式,李泽厚给予了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高度评价[19]。假如没有这种仪式符号,每个个体情感所汇聚而成的社会情感就可能会不稳定地存在。可见,仪式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将情感固定化与持久化的作用。一般参加仪式的人都心有体会,它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安宁、平和、激动与热烈。
彝族原始文化多重观念的延续,亦成为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动力因素之一。从某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大家可以将文化观念理解为一种惯性之力。这种惯性之力乃文化积淀的结果。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应至少包含彝族族群源初性的图腾、民间信仰仪式、灵魂、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各种观念。在此力作用下,彝族丧葬仪式活动一以贯之。这里的“一以贯之”特指两方面:一是彝族丧葬仪式活动本身持续开展的不间断性,至于其以什么样的形式,则跟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一直在变化,形式的变化并未取消活动本身;二是彝族丧葬仪式活动的核心内涵——对生命的崇敬与救助一以贯之。
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是上述五种动力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运行具有内在机理。第一,其起作用的是彝族丧葬仪式的核心动力——本源性动力,由仪式的源生力——“崇生”意识、需求的内驱力——两界利益诉求共同构成。第二,本源性动力的发生还受呈现性动力的牵引,以此促成丧葬仪式的举行,并借此聚集、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这种激发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被礼化的情感和原始观念。第三,仪式的举行还需要被监督,可称之为监督性动力,只有监督,才能确保丧葬仪式在社会可接受的界限范围内举行。这种监督实际是同丧葬仪式动力机制相制衡的平衡动力机制的运行,正是在上述三种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丧葬仪式才得以进行。可见,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是各种“力”之间相互限制、相互约束与相互制衡的结果。
仪式的源生力——“崇生”意识、需求的内驱力——两界利益诉求,共同构成彝族丧葬仪式的本源性动力。所谓本源性动力即指最根本、最重要的动力。没有此动力,其它一切动力都将不复存在。需求的内驱力——两界的利益诉求,即生死两安之下的安全需要、生活需要等各种需求,是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主体性动力,即直接动力或内在驱动力,因人的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赖以发生的根据和动力。丧葬仪式只是利益诉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达成目的的可靠性手段。此种利益诉求实际只是想象性结果,没办法得到验证。因跟着时间的推移,生命总会延续,福、禄、寿也有一定可能会随之而来。因此,此种纯粹思想构建的产物似乎在某个时期内得到了某种验证,即使后面的结果很糟,也总会有其它的理由对此进行弥补以重新诠释。
仅有主体性动力,还不足以全面解释彝族丧葬仪式活动何以发生。彝族丧葬仪式作为人活动的一种对象,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源发的力量,可称之为客体性动力,即彝族丧葬仪式本身就具有的“崇生”意识。如果丧葬仪式活动本身不具有此意识,仅有主体性动力下的主体性活动,则我们今天所见的彝族丧葬仪式活动的形式与程式,尤其是活动本身所承载或源发的力量,肯定与现存的不同。当然我们没办法否认的是,从某一种意义上讲,任何活动都是属人的活动,人是一切活动的起点与终点。彝族丧葬仪式内蕴的“崇生”意识仍然是人赋予的,仪式的存在,是为满足人需要的表达形式,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可行性路径。
正是基于人本身的需要,以及彝族丧葬仪式本身能提供和满足主体性的需要,从而才促成了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但仪式举行同样需要情感的激发和牵引,还会受到原始观念企图呈现的刺激。因此,就必须引入监督机制或平衡机制,于是就有了平衡性动力,该动力主要从平衡机制的方面就彝族丧葬仪式的界限、活动的“规范”、情感表达的限度与原始观念呈现的尺度等进行划定,以确保彝族丧葬仪式在社会可接受的“度”的规范内圆满举行。
人性礼化的表现力——情感、观念的延续力——多重观念,是彝族丧葬仪式的呈现性动力。亡者的去世,刺激和激发了亲人生者的情感,这种情感相当复杂,但应以悲痛、伤感等情感为主导。人的此种情感需要表达,因此它不断激发人的内心,企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活动,表达自我感情,正所谓“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22]但这种情感的表达形式可能会存在某种异化,其异化的表现之一即将内心的真实情感显现为某种过度夸饰,此夸饰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在陆CY 献祭仪式上②共来了十四支吊丧队伍,其中三儿媳娘家队人数多达160 多人。如果我们将此种夸饰看作是外亲表达情感的异化,则郝彧等针对凉山葬礼的实际调研结果则显示的是主家表达情感的某种偏颇,主家尽力将丧礼办得隆重豪华,以此赢得别人赞美,获得好的声望[4]。这是情感表达异化的一极。此种情感异化的表达方式既造成消费的非理性化,从某一种意义上讲,亦可能淹没了自我内心的真情实感。情感表达的形式异化了人的感情,换句话说,形式异化了感情,感情受到表达感情形式的控制。
情感表达还也许会出现另一极,即对亲人亡者的去世无动于衷,表现出冷淡、漠不关心,因此亦不存在借助形式以表达情感的形式。如此,社会伦理道德就会强制进行情感的确认。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随着日常生活的琐碎,某些情感会被消耗殆尽,这将不被社会所允许。社会总会通过种种形式,当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仪典,不管仪典的“重要性多么小,它都能够使群体诉诸行动,能使群体集合起来,举行仪式……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12]476
彝族丧葬仪式除了成为情感表达的形式,其形式本身还呈现出更多彝族原始观念,如巫术观念、灵魂不灭观念、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等观念,这些观念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成为历史积淀的成果。作为成果,其呈现与表达并非主观意识所为,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具有非自觉性与非理性。同时,彝族又具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该意识的表征之一乃对历史的看重。对历史的重视可能意味着对上述观念的追忆。因此,这些原始观念的呈现又增添了新的动力。于是彝族原始观念可能会在彝族丧葬仪式中大量显现,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观念存在一些糟粕,需对其进行严格“监控”。
可见,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界限”,实际乃是对情感进行“度”的把握,对原始的一些观念和集体意识的“监控”,这种把握与“监控”主要是根据伦理道德与社会理性。此种监督构成彝族丧葬仪式的监督性动力,它是作为一种平衡性动力运行和显现的。
规制的强制力——伦理道德秩序,作为社会理性,是彝族丧葬仪式活动举行的监督性动力,或称为平衡性动力。相较于情感的激烈性与复杂性、原始信仰的非理性与“酒神”性,伦理道德更具平和性与理性化。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外在与内在的行为规范,对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既起着监督的作用,又对其也许会出现的过分情感与观念进行控制。
这种监督从表象上看是对彝族丧葬仪式的形式、规模与程式,即“礼”的规定、要求和标准,但从本质上讲,是社会对其成员施以权威,以规范约束其行为。根本目的是确保社会成员的活动不违背社会运行的道德一致性与逻辑一致性,从而杜绝不和谐局面的发生[12]19-20,以维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可持续性。当然,社会运行的道德一致性与逻辑一致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跟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发展。
彝族传统的献祭一般要求牛、羊、猪三牲和鸡。后随着人的意识逐步的提升,为避免造成严重浪费、避免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避免对环境污染以及迫于经济压力,大致在民国时期,贵州省的毕摩召开了一次会议,对献牲作了统一规定。献祭由过去的牛、羊、猪三牲基本变为现在的一祭牲如绵羊。可见,这种丧葬礼俗已根据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但它并未违反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一致性与逻辑一致性,且被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这种调适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密不可分。从中我们亦能把捉到社会运行的道德一致性与逻辑一致性的“宽容”。
可见,彝族丧葬仪式的成功举行,是在本源性动力、呈现性动力、监督性动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有效实现的,其中本源性动力是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核心动力,呈现性动力主要起着一种表达和牵引的力量,而监督性动力则为仪式的举行划定着界限。正是在如此有序的动力系统内,丧葬仪式才成功举行,亦确保了仪式的核心功能——救赎功能的达成。
彝族丧葬仪式承载着彝族生命意识,表征着彝族死亡文化的独特性,其存在的动力元素包括“崇生”意识、利益诉求、伦理道德、秩序重建、多重情感与观念延续等。在本源性动力、监督性动力和呈现性动力相互作用下,彝族丧葬仪式活动延续不断。它的举行既呈现了其源生的“崇生”意识,又持续不断地强化此意识。因此,彝族丧葬仪式的核心功能——救赎,之于重建社会秩序、增强民族认同感与道德教育等功能具有奠基性。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彝族其他民俗祀奉仪式、神话传说、节日仪典与毕摩经亦含有浓厚的“崇生”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以为整个彝族文化都富含“崇生”意识,并认为这是其文化的核心内涵和较为独特的智慧。可见,彝文化从自我文化的核心内涵上,真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因中华文化是一种“生”的文化,鲜明之处在于“终极关怀”的共融[23]。因此,本文基于彝族丧葬仪式动力机制的研究,或将具有普适性意义。当然,我们应舍弃彝族丧葬仪式中残存的落后与迷信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处理好扬弃与继承的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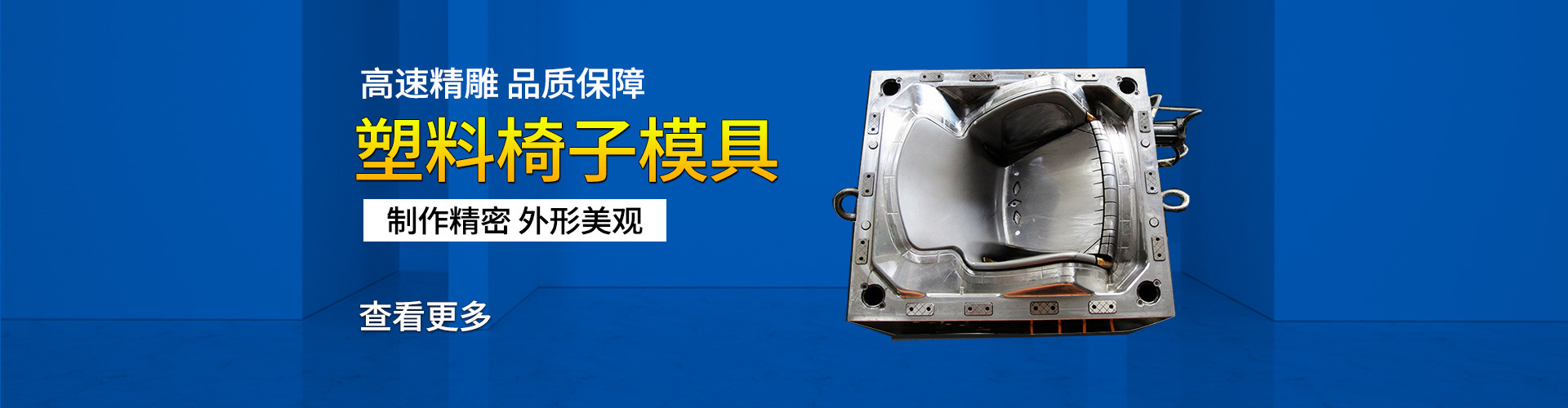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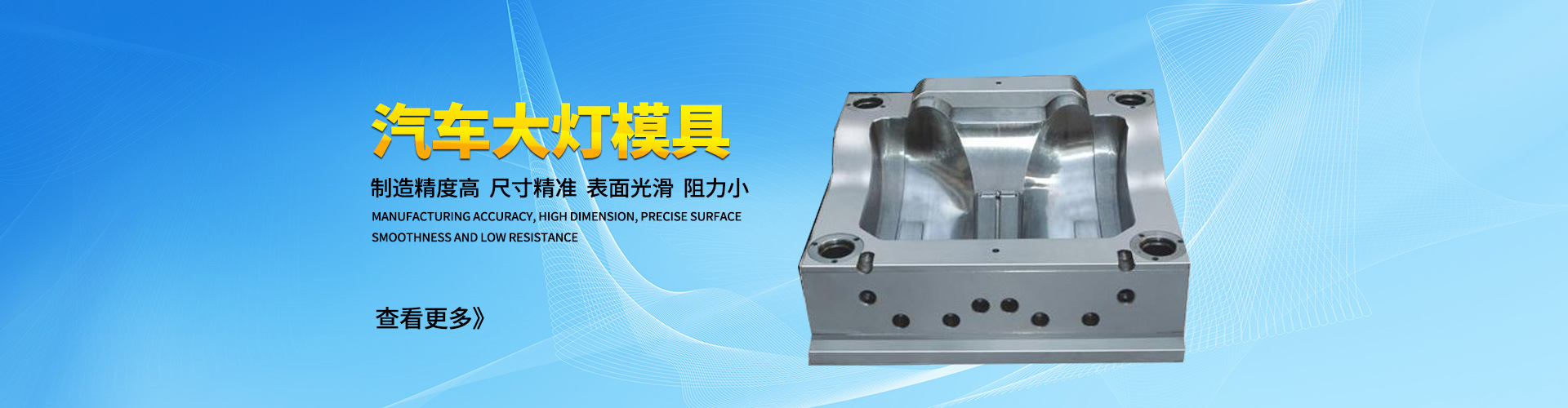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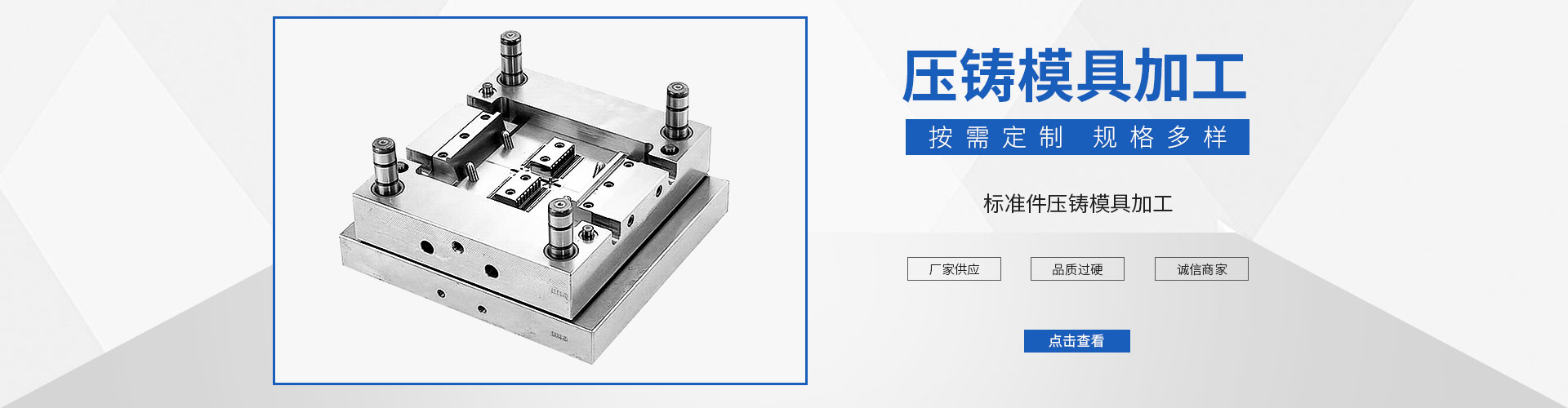
 更新时间:2024-06-14 01:29:43 来源:
更新时间:2024-06-14 01:29:43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