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交头接耳,没有手机亮起,这部在蒙特利尔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国际电影盛会上获奖无数的片子在安宁中开始又结束。
张蠡此时人在四川,他回忆半年前头一次来大凉山,就为了拍摄《我的圣途》。
如今电影得奖了,上映了,这部作品似乎也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眼前周遭的一切亲切又熟悉。

故事大概是这样:彝族一位毕摩(祭师),沙马达伊年少丧父,看到死不明目的父亲,他励志要完成父亲未完成寻找白色圣地的使命,途经布希莱托这个寨子时与阿几一家人发生了一连串的爱恨情仇。
少数民族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用电影作为载体来关注的人显然不多,那么,张蠡导演怎么想到把《我的圣途》搬上大屏幕呢?
“第一次接触彝族的文化,是在十五六年前”,张蠡当时创作一个剧本时,认识了凉山歌舞团的团长,同时也是一名彝族作家——克惹丹夫。他当时读过克惹丹夫的一部小说《山神》,深深地被吸引了。后来,小说《山神》也成为了《我的圣途》的故事基础。

但那时,《山神》已被原作者拍成一部电视剧,整部戏在凉山一处荒芜的地方取景,讲述了彝族毕摩(祭师)、苏尼(巫师)之间的故事,但在内容上主要对准彝族封建的文化和黑暗的角落,最后在四川电视台播出时遭遇腰斩。
张蠡是内蒙人,同样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他,对神秘的彝族非常感兴趣,但真要拿在手上把它雕琢成自己的作品,是十几年后。或许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直到2015年,一个契机出现了:张蠡认识了本片在加拿大的合作方,“他是我多年好友,也是移民多年的华人,他说中国电影在本土很热闹,在海外市场也很好,但他不想做娱乐性的东西,更想做些有世界语言的,也就是民族的内容,阐释人类共有的价值观”。片方希望做这个主题:在中国人中,有些人是有信仰的。“但现实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信仰”,张蠡要找到有信仰的群体,写他们的故事。

于是,十几年前与《山神》的接触,成了张蠡今天成片的伏笔:从彝族诗经中,他了解到彝族人有个一直求索的白色圣地,不知道在哪,谁也没见过。“我就从彝族几代人执著追寻白色圣地上着手写故事,追寻的人在途中遇见各种坎坷,但不改初心”,张蠡希望,用这故事承载现代人对理想、信念、信仰的追求。

张蠡创作时查资料研究彝族,这是个文字、语言、信仰几乎独立于其他民族的古老民族。“他们文字甚至比古汉语还更早,诗经传承也很好,有很多流传的故事,这个民族很独特,人种上来说黝黑皮肤、高高鼻梁也不相似大多数中国人”,这神秘的民族对观众很有吸引力。
在背景设置上,他定格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值乱世,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谁也顾不上这偏僻的大凉山,彝族的民族文化也较为纯粹地被保留下来,“虽然现在逐渐被同化,古彝语都罕少有人说了,但当时是比较原生态的彝族环境”。在影片中,主角的一路圣途,遇见的人跟事更是地道的彝族味。

“我更希望极致电影化,艺术氛围更强烈,用执拍手法,镜头直晃得人心发慌,一开始拍摄纪录片的色彩更重,但中途放弃了《山神》中穷山恶水的暗黑故事”。找遍大凉山全部地方,直到冕宁县一个美丽的牧场,张蠡决定做个反差:让画面静下来,美景之下,故事本身却波涛暗涌,这个暗涌,关于人心、权力、欲望:“大自然的确很好,其中部分丑陋的东西,要深挖下去才能看见,根本上还是传达信仰与真善美”。
除了环境,演员也是原生态,充分融入当地生活状态。“陶多多(该片女主阿几的扮演者)是加拿大华裔女演员,我们收了她的手机,把她扔在大山的茅草屋里整整23天,让她啃着土豆,砍柴放羊,最后这位从小生长在海外的姑娘被晒得黑乎乎,浑身脏兮兮,一嘴古彝语,浑似阿几本人”。现在的演员罕少这样静下心来塑造人物,也罕少能如此投入地去诠释这样厚重的故事。
彝族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百年来却没人为其制作一部作品。张蠡更有些文化传承的意思在里头。而影片在海外备受追捧,北美欧洲人觉得故事新鲜,意大利人觉得相貌亲近。张蠡总结为:批判丑恶,颂扬美好,这是人类普遍的信仰、民族之间共通的价值观,“用世界性的语言叙述中国少数族裔的故事,甚至从这个民族延展到整个中国的文化内涵——我们文化输出的初衷达到了”。
张蠡对此坦承:出品方不愁投资回不来,因为韩国已签约,欧洲北美很多片商来买版权;但在中国本土上映的情况不太均匀。
坐标北京,笔者在网上只查到一家影院在上映,且当天排片只有14:25、20:25两场,而张蠡介绍,成都、深圳、海南的排片情况也参差不齐,总之不算很好。
两天前,那场只有5个观众的观影经历中,笔者也禁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这部豆瓣评分高达 7.5、有思想味道的佳片为什么就是没人看?

“首先,大家对演员不知道不认识,故事本身也没什么话题性,这部剧情片本身很厚重,跟现在市场上那些容易获得观众的喜爱的热闹欢脱的喜剧片,或者拥有精彩视觉效果的大片不同”。尽管如此,张蠡在认真讲好故事的同时,也在创作中尽力融合了悬疑、暴力、战争等相对商业的元素,因为他深知在国内当下环境中,电影纯玩艺术基本上没有出路。考虑到观众的口味,他做了妥协:“毕竟外方投资也想试试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
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大的财力用来宣传:“本身拿到的投资并不多,这笔钱怎么花就很关键;而我们主要分配在制作上”,他苦涩一笑:“另外,实在很难跟外方的投资人解释清楚,做了一部好作品,为什么还要花几百万、上千万做宣发。”

本身题材的小众,再加上宣发不力,所以在商业片占主流的院线,《我的圣途》没有很好的排片:“这片子抵达不了主流观众群。到了院线经理,一听这名字就是文艺片,再一听是少数民族的,他们就说算了吧”,张蠡期待片子口碑的发酵,但无力抗衡当今市场:“中国喜欢看喜剧,看视效,但电影类型也应该丰富,娱乐完了,还有片子让你坐下来沉思”。
而《我的圣途》悲情厚重,显然与主流电影审美相悖。但这部片子开放的地方在于:“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圣地,为了心中的圣地必须使劲往下走,这里面有对人性的鞭挞。对我自己的创作是相同。”
在丰富影视类型这个点上,行走中国电影界三十年,执导过多个题材的张蠡说:“韩国的安山电影节上给我做了作品回顾展,在他们眼中我这种导演很奇怪:怎么跨度那么大!”
原来,张蠡这几十年中,从来不给自己贴标签,拍过给90后看的轻松活泼的爱情戏,拍过厚重的人文历史题材,也拍过又红又专的主旋律。不像韩国电影导演分类那么明显,有些就是爱情戏,有些是惊悚类,金基德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包括一些中国导演,也擅长一种题材,一辈子主要钻研一种题材,浑不似张蠡这样在不一样中跳跃。
张蠡坦诚自己有些“不安分”:“有些人会觉得,这也做那也做不安全,你既然是这种风格,那就循规蹈矩去做,一直这样也不费劲。可我不喜欢在一个状态里呆很久,不停地拍一种东西,我十分喜爱没涉足过的东西”。
这种性格带来的优势,大概是乐于用各种主题、各种题材、各种表达方式拍片子;换个角度看,每次跨题材都要做很多准备,带着创作热情摩拳擦掌,这种琢磨不但能激发灵感,还能刺激个人积累。

“做每部片子其实都是学习的过程。我们真的很需要静下心来看书,行业中不学习的人太多,我特别怕被污染”。大家好像觉得这行业门槛很低,是个容易敛财的渠道,都着急忙慌地接戏,也不琢磨作品给了观众什么:“很多时候要创作者自己达到了一定层次才能给观众一些东西;要是自己都不达标,怎么对观众表达?”
2003年左右,他对自己拍摄的作品没了信心,于是花了六七年跳出来,不拍电影电视剧,而是做纪录片,特别是人文历史纪录片。“纪录片是对你个人文化素质考验较高的作品,因为你首先要自己写稿子,解说词不光有主题内容,也要有视听语言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横向、纵向挖掘深层次的人文社会的东西。”
这几年,张蠡历经疯狂的学习积累期,自然不自然把学到的东西融化在作品中,于是迎来创作的丰产期。
“这几年有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不管是家庭婚恋,还是公安涉案,对这些题材都特别感兴趣”,张蠡特别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状态,但当时的社会积累、经验知识储备都不够。“三十岁之前的作品很单薄,爆发力不足;现在要做啥东西,就翻来覆去把它琢磨透彻。这其实也符合电影工作者的成长规律,导演界50岁之后更容易出好作品。特别是想创作能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就必定要通过时间积累有个厚度。”
在积累与沉淀的反复中,张蠡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对自己扮演的导演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选择执导项目时,首先他要求是自己的团队,“长期磨合后,大家更了解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制片方给予特别好的创作氛围,“哪怕一开始我对主题不是很喜欢,或许也能做个很好的作品,而不是接了特别好主题,方方面面涉,那就完了。”

他认为一个懂得电影创作的出品方、制片方,比获得一个好的主题更重要,因为获得信任和创作的自由之后,导演个人的发挥才愈加完整,也容易出好作品。
个人发挥中,张蠡习惯给自己“定目标”:“起码比片方更高。因为拍电影是综合事件,创作过程中各环节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肯定要减分。我们一开始就给自己定90分的目标,这样就算削减,最后也不会低于80分。为达到这个分数,在故事叙述、内容读解上一定要非常扎实,且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本子。”
对于任何制作环节,美术、特效、灯光、服化道等,都要遵守最高标准。比如,《我的圣途》声效找的是国内顶尖的和声创影,张蠡要求做出电影院300人巨幕那种状态混出来的电影音效。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位专注创作中每一个细节的导演,面对当今中国电影百态也忍不住一声叹息。
中国电影市场上有个怪相:赚钱的导演,并不全是口碑导演;口碑导演,或许没那么挣钱,市场表现与作品口碑似乎成了衡量导演的两种难以交融的标准。
“这是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能够造成的。有些人给大家补充了电影类型,满足了部分需求,比如,有些被称为“项目经理”的导演;另外,有些执行导演,摄影师,监制,在行业内工作了几年,欠缺作为导演的专业素质,就企图跨界拍片子。”他们也许挣了钱,但张蠡疑问:“有些电影看过了就不想再重看,有啥意思?”
他更崇尚纯粹的影视作品,像李安、侯孝贤、贾樟柯,带着敬畏之心,认真、不低级地做电影,而不是做商品。只有这些作品才能在电影史上留下关于中国的纪录:“比如,从《小武》、《站台》中感受到浓浓的80年代社会环境,侯孝贤对台湾社会和文化的表达,李安跨越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辨,他们用镜头记录的痕迹才是一种历史。”。

令张蠡遗憾的是,在中国,时代科技的进步降低了影视行业的门槛。“以前拍电影很神圣,就那么几个大电影厂,不是谁都能进来,一定要经过好的教育与培养。厂里也不能随便拍,甚至有些做徒弟直到50岁才有资格自己拍。”国外工会也是如此,导演在工会并且有资质、有水准才能拍,这就是规矩。
张蠡感叹:“国外电影人拍片子,不是观众决定,而是影人做了东西,再引导观众去看;可中国影视公司的策划部门彻夜开会在干嘛?分析市场、大数据,分析怎样迎合观众喜好的点,去加工电影”——如此, “是我们给观众生产娱乐品。甚至我们也成了艺人,被归到娱乐圈,从艺术圈到娱乐圈,咱互相娱乐,那就完了。”

当大量题材雷同、内容劣质的作品被搬上银幕,中国的观众也渐渐不买账了,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遭遇滑铁卢。
张蠡却以为这是件好事:“别一味地追求数字,首先应该规范市场,引导大家在良性的市场循环中往前走。“去年市场的急速爆发蒙了大家的眼,以为中国市场已到了茁壮成长的阶段。”但其中很多东西并不好,比如,偷票房,影片发行时,片方自己要掏钱买千万票房,伪造片子很热的表象,从而吸引流量。“包括《叶问3》,其实是一只出头鸟,资本操纵太明显,随后很多大片也被连着调查,他们的票房都有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挤出水分留下干的?”

除此之外,去年还出现不是电影的东西来冒充电影的乱象,比如真人秀节目的电影版,“有些节目编导把电影做成了电视转播。也算受欢迎,但观众越来越成熟,80后已有自己的选择,90后、00后也有糊弄不了的时候,这些不着调的东西还是趁早撤了。”
张蠡认为,现在电影应该回到电影本体,一定要有门槛,按照电影本身的创作规律,创作真正的电影,而不是伪电影,或者类似电影的东西。“这些市场泡沫,挤出来的过程或许漫长,但对中国电影发展来说都是好的。”

市场行为需要规范,但电影创作不能过度规范。“我们每年在政协两会都呼吁电影分级,不要阻碍发展,给电影松绑”,但哪怕审查制度仍旧严格,也不能因为偷懒放弃想要表达的题材。“创作者不带脑子:我们玩吧,只要能逗乐观众,这样肯定不行”。
张蠡呼吁:“咱们不可以回避现实,不能天天谈恋爱,也不能总是喜剧魔幻。你活在今天,生活在这个环境,呼吸这里的空气,遇见周围的人,你的文化,你民族的历史,电影得给予人们关怀,得做时代和心灵的记录者,这才是我想探讨的东西。”

“每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都有烙在灵魂里的痕迹。日本电影就像日本的气质:安静,沉浸。美国的电影像它的文化一样开放热情。导演能在作品中心平气和、稳稳地说一个故事却让观众热血沸腾,这就是本事。可我们太着急了”。

那里或许没有传说中“白色的马,白色的房子,穿着白色衣裳的人”,但有张蠡在坚守与统一中越来越返璞归真的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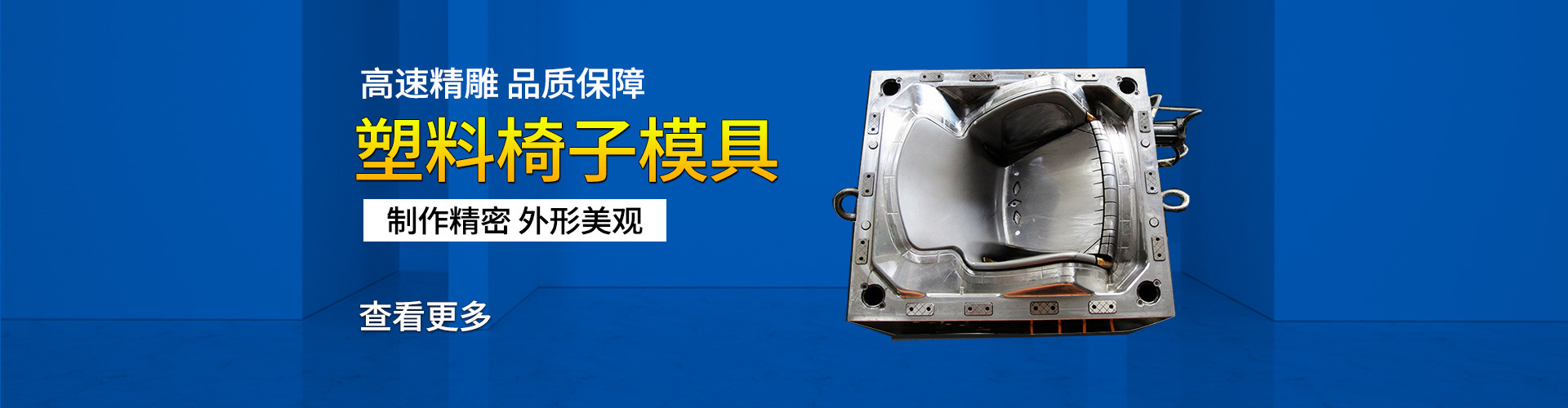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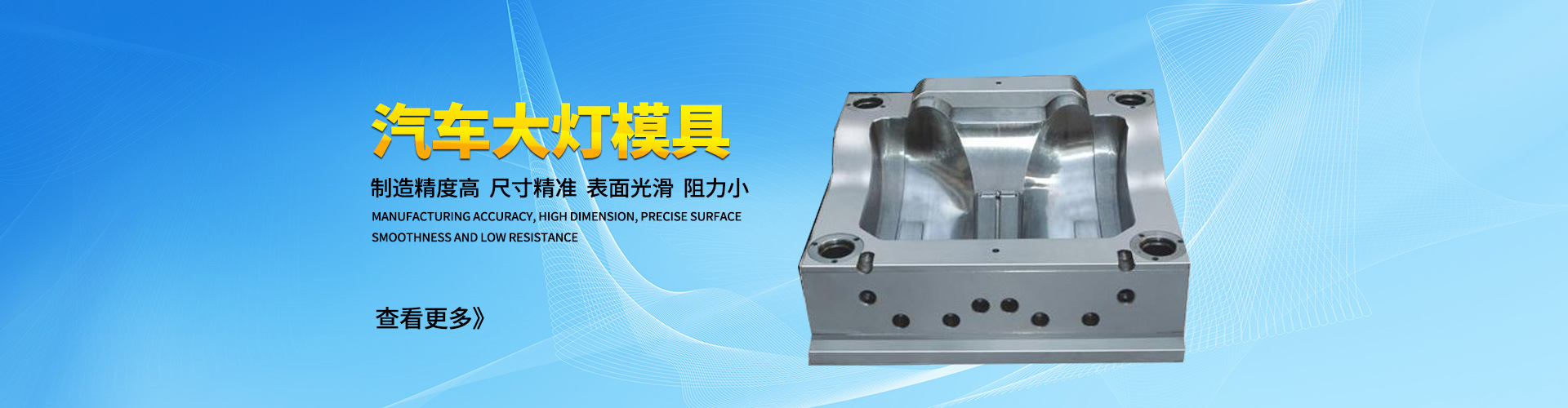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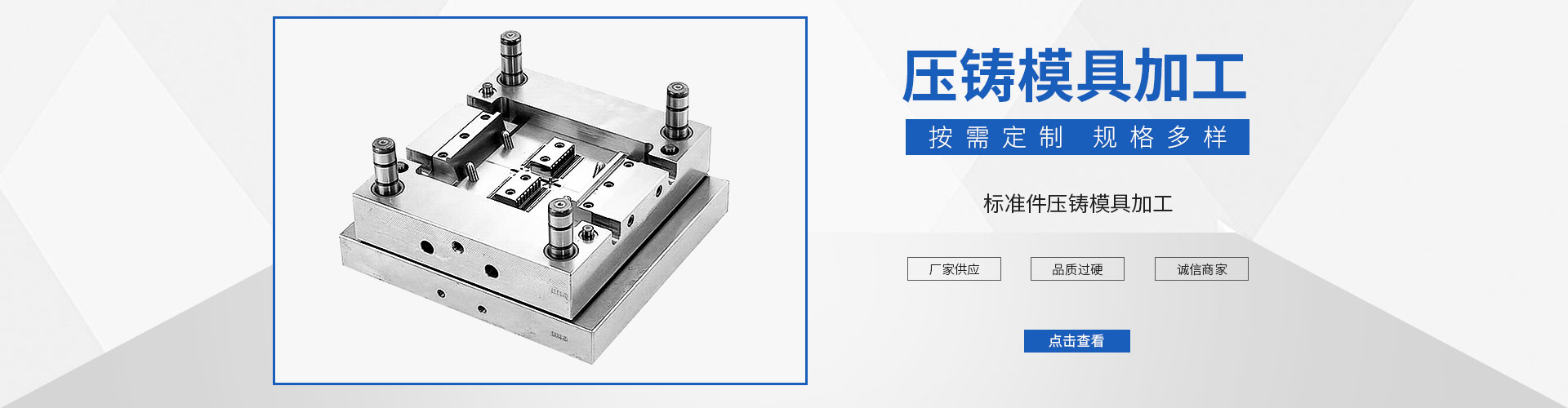
 更新时间:2023-12-13 13:18:00 来源:
更新时间:2023-12-13 13:18:00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