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上的声音”音乐采集计划由音乐人赤沙、刘俊麟发起。他们自2019年起,走访彝族人生活的地区,共采集民间歌曲、器乐曲、故事五百多段。保存珍贵素材的同时也在其基础上二度创作,最近推出新专辑《原野上的声音·彝族合辑》,去参加了的音乐人也包括莫西子诗、泰然、沐诗乐队、JIHU、海日乌芝、俄木旺堆、吉克克牿、KUN。
这张专辑是一次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创新,对你们来说,一个真正有机的理想过程是怎样的?
原住民艺术、音乐的创新和发展有一定的滞后,但现在突然有很多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是其中之一。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以前很多地方磨麦子是在水流湍急的地方弄个水车,就有相应的拉水车的歌等等。这样的传统生活方式差不多要没了,所以最民间最原始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然也会消失。怎样在这个时代做创新,实际上也是我们从始至终在探索的,对“理想的”还没那么确切的答案。
我刚开始做时比较坚定——采集保留传统的,在其基础上二度创作新的,再通过种种方式去传播。现在也有点迷茫,这四年经历了很多,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别的方面都很有压力,自己有转变也有妥协。我们俩经常从别的地方挣钱用于“原野上的声音”,有一年我把研究生学费都拿去采风了,毕业时才补上。录专辑、采风都需要很多钱,做出来以后听众也不一定感兴趣……
不过现在我们计划在五年内至少集齐八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曲库,把采集到的各类民间音乐分类、注释、上架,可以让学者搞研究,也可以让本民族的人溯源。也发起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采录身边的民间音乐上传,从而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减缓民间音乐消失速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尝试寻找商业模式,总的来说就是想办法赚钱,想办法一直做下去。
除了赤沙说的这些点,还有反向压力。就像最早把古典吉他变成电吉他时,当时被欧洲古典派口诛笔伐得很厉害一样。我们现在当然比那会儿好,但是依然有类似的情况,还是会有当地很坚持传统的人说,你们怎么能把像是毕摩神圣的经文之类融在这样的音乐里?!这是亵渎!诸如此类。
但这点其实也有两面性,也是有好处的。正如正是因为古典派的存在,西方古典音乐那套体系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得它和别的音乐的碰撞成为可能,才有了现在创新产生的各种现、当代音乐。我相信这个积极的图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潜力更大——民族实在是多,传统也还能找到相对完整的。
俊麟在记录你们云南彝族地区采风之旅的纪录片《之南》()里,提到少数民族音乐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音乐有一个特点就是旋律的重复,这和电子乐的特性也很相近,是一个跨时空的交流。能展开说说吗?
我非常早之前就发现了这个特性,我的分析是,民间音乐和电子音乐有很接近的一点,就是都是直接从人的本能出发。
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重复还因为它的基本功能、目的不在音乐本身。打歌时的芦笙或者大三弦还是以辅助娱乐为主,旋律是否有变化他们不关注。彝族民间歌曲的重复在于群众要强调所表达的心意。一般宫廷音乐就很少重复,因为皇室要观赏。
纪录片里比较详尽地记录了你们在云南的采风历程,四川彝族地区的采风记录资料不多,能说说那里的旅途吗?
我们是从凉山开始的,也是第一次采风之行给我感触最深,正是通过它,我们明确了“原野上的声音”要记录的究竟是怎样的声音。
2019年1月,我们的第一站是凉山文化腹地美姑县。第一次出行条件有限,准备也很仓促,但却是最有收获的,采集到的内容甚至比之后的采风都丰厚。
刚到美姑时还下着雪,我们四处打听寻访民间艺人,去文化馆问,也托朋友找,后来找到一位据说十分厉害的民间艺人,常上央视等大型节目,也参加各种演出活动。几经周转约上了他,但沟通后意识到,其实我们想找的是更原生态的,这些人可能在技法上没那么好,但得是“去舞台化”的。
我们内部商量决定把重心转向村庄中更“普通”的一些彝族人。随后的半个月里,我们开着车穿梭在美姑的各个乡村角落,一路上碰到人就打听村中是否有会唱民歌或是会弹民乐的人,后备箱里装满了啤酒、酸奶、糖果、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许多不那么“著名”的民间歌曲、小调旋律。这样的一个过程所带来的体验本身也非常难得,在后来的整理工作和二度创作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在彝族地区做过三次采风。第一次是凉山州的美姑县、昭觉县,第二次是布拖县和甘洛县,第三次是云南,大理的巍山县,还有丽江、楚雄。
其实在我跟赤沙一拍即合要做“原野上的声音”采风之前,我自己去过一些羌族和藏族地区采风。在彝区,如果不会彝语,有些偏远的地方是真的进不去也无法采风。第一次到美姑县时触动很深,很多彝族朋友尤其是小孩的眼神真的吓我一跳——我从没见过那么干净的眼神。这是一种很直观的对心灵的冲击,而且当时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眼神,心里莫名的有点羞愧,就是有一种自己脏的感觉(笑)。
三次都是我们自己租车开进去,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细节是第二次在布拖采风时,那天很晚了,我们拜访、采录了一个毕摩,回县城的路上碰到错车,但路窄,赤沙倒着开了两公里才错好车。诸如此类的细节其实特别多。
彝族的毕摩管人间的事,就是病灾这些;苏尼负责跟上天沟通。这不是通过师徒传承学到的,往往是,比如说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自己就会了。有很多相信万物有灵信仰的部族都有类似的逻辑。
第一次采风在雷波县遇到的毕摩赤古比较特别,他既是苏尼也是毕摩。他还专门为我们做了一个苏尼仪式。我们把整个仪式都采录了下来,也用它做了新创作,融入新音乐,出现在第一张唱片《山》的最后部分,也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很震撼、很实验的一段。这首纯音乐里还有另一位美姑县巴甫村的毕摩,他让我们录了很多唱词和说词。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在成都和北京开音乐专场,把苏尼也请了来。他从来没出来过,但绝对没怯场的感觉,这个人的气场特别强大,苏尼嘛。
其实接触了彝族的毕摩、羌族的释比、藏区本教的贡巴甚至是北方民族的萨满后,我个人觉得,当今的哲学甚至是科学都该朝这个方向深挖一下,不该完全忽略。这当然不是让人去贩卖神秘感,我们自己也不会这么做。
我们前两次采风遇到过很多毕摩、苏尼,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采风,也就是2019年7月在布拖。那时是火把节,布拖最盛大的节日了。县城里挤满了盛装出行的人,在人群中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位留着脏辫的毕摩。我自己是彝族,从小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长大,但“阿都”地区(指凉山州金阳县、布拖县、普格县等地)语言和文化上都跟其他几个土语地区(凉山境内大都使用彝语北部次方言与南部次方言,北部次方言为1.圣乍土语、2.义诺土语,南部次方言为1.布拖土语也称阿都线.会理土语也称所地话)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所以当我看到背着法器与法帽的毕摩留着脏辫时,还是十分好奇。
我们跟他表明了来意,他说自己来县城是受邀参加火把节开幕仪式表演的。他家住在布拖县城十几公里以外的拖觉镇。晚上十点多火把节活动结束后我们开车送他回家,一到家,他就从箱子中取出很多旧经书开始诵读。虽说阿都方言我一半靠听一半靠猜,但诵经的调式还是唤醒了我的感官记忆——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听毕摩诵经,很有小时候在阿嬷家的感觉,心中涌起一阵温暖。俊麟提到的错车就是从这儿回县城的路上。
这位脏辫毕摩的声音也用在了《兹兹妮扎》的开头。兹兹妮扎其实是一个毕摩经书里的故事:
相传在远古时,彝族大英雄热地说夫和他的弟兄们一起漫游四方,有一天他们走进了德布罗莫——彝族传说中众鬼聚居的地方,是彝族人的禁山。
傍晚,他们投宿一间金碧辉煌的房子,但里面只有无数骷髅,空无一人,这让他们很诧异。过了一会儿,这家人陆续回来了,他们虽是人样,但言行举止很怪异,旁敲侧击下他们得知自己是来了食人魔王的家。热地说夫他们也假装是食人族,伺机逃脱。
晚饭时,食人魔王叫下人去牵一头牛来招待客人,捆来的却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为了不让魔王怀疑,热地说夫和兄弟们很自然地拿起人肉,再悄悄换成自己的兽肉大嚼,魔王更加相信他们是同类,也放心地吃喝起来。
晚上,据热地说夫暗中观察,魔王一家人都变成一个个蜜蜂,在蜂巢里睡觉,最后一个飞进去的是小女儿兹兹妮扎。热地说夫和兄弟们半夜悄悄起来堵住蜂巢口,但住在最外面的那只小蜜蜂逃了出去。蜂窝和里面的蜜蜂被烧尽,残灰倒进河里,食人族从此从大地上消失了。
那只死里逃生的蜜蜂变回了人形兹兹妮扎,后来她还变成过各种山间动物——鹿,山鸽,山羊,豺狼。有一天变成一只白獐,遇到打猎英雄哈伊地古,她清楚自己逃脱不过,只好苦苦哀求,但好话说尽,哈伊地古还是射了她一箭,从头穿尾,獐血喷涌而出。
居住在兹兹普乌(彝族传说中的发源地)的猎人阿伟列库狩猎时,有一天追着一只公獐到悬崖边,公獐突然不见了,只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坐在树下,他们相恋并结婚了。
这位妻子温柔贤惠,对阿伟列库很是体贴,但很奇怪,她煮饭一会儿就熟,织布速度奇快。猎人去问村里的老毕摩,后者告诉他他妻子是个鬼怪,必须除掉,否则会祸害整个村寨。
在毕摩的授意之下,阿伟列库装起病来。他说自己得了一种怪病,需要阿白角鹿胆,兹兹妮扎取来了鹿胆。阿伟列库又说需要白色的雄獐胆,兹兹妮扎也给他取来了。他又说了一堆药,无论多难,兹兹妮扎都为丈夫找来了。阿伟列库见这些都难不倒兹兹妮扎,又说只有马迪和初山上的白雪才能治愈自己的病。
去马迪和初山的路很艰险,但为了丈夫,兹兹妮扎豁出去了。临走时,她万般叮嘱丈夫不要请毕摩做法事。
阿伟列库满口答应,但兹兹妮扎前脚一走,他后脚就请来毕摩做法事,连续三天三夜。兹兹妮扎在去马迪和初山的路上,头脑发胀,最后变成一只红山羊,她没有忘记丈夫的病,用羊角带了一些冰、蹄子夹了一些雪,最后昏死在一条小河边。
几天后,小河涨水,把山羊冲到下游,被几个割草的妇女烤着吃了。这些女人变成了厉鬼,世间从此有了祸害人间的鬼怪。
赤沙提到“去舞台化”,苏尼到北京、成都的现场,实际上也是把他请上了舞台吧。你们是怎么平衡“去舞台化”的?
我所说的“舞台化”是指民间艺人长期受表演环境影响,还有别的随之而来的各种附带的心理变化。我们将毕摩请到北京和成都的演出中,给他架一支麦,告诉他在村里作毕时是怎样现在就怎样,我们想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情况。
我具体讲一下我所理解的赤沙说的“去舞台化”吧。这些年有很多民间艺人被媒体、各种组织发现,然后上电视,甚至是综艺娱乐节目。他的精神面貌就慢慢变成了一个跑通告的人,家里到处放着奖杯,采风遇到他时,说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自己当时在电视台录什么节目、发生了什么,甚至说话都油了。当一个人在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他的音乐也一定会变的。
我们把苏尼请到成都和北京做开场,请他以最自然的方式演示一套仪轨。没有在他身上做任何修饰,都是在舞美上做。
对我来说还是在于发现不同土语区的差异之大。我自己是凉山人,但从没去过阿都地区。故乡甘洛离成都比较近,而且在好几十年前就通火车了,所以甘洛人更多是往成都走,再不济去西昌,很少去凉山腹地。尽管如此,采风过程中,我更深地接触到了跟甘洛有差异性的文化内容,它们能唤醒我心里的感官记忆。
最大的感受其实就只有震撼。来自两方面,一是音乐、旋律本身,二是我惊奇地发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观、宇宙观。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些都是支离破碎的。从这点来讲,我还挺羡慕他们的。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万物有灵。我觉得这种坚定不移的相信是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我们的生活氛围里,对任何东西都是半信半疑的。反正坦诚地说,我是没有体验过坚定不移的相信这种感觉。
走到越偏远的地方,当地人就越纯粹。生活环境格外的简单,人也就简单,他们的情绪反应、行为都没什么目的性。近距离跟这样的人接触是能被感染的。
他们和自然的相处模式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和自然的沟通。而且不能说自然只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或是两者依存之类。这么说吧,当地人的笑、言谈举止、情绪都特别“自然”,就是自然。
他们也根本用不着像我们的生活节奏里面的人那样各种面具戴着,还有各种面具换。反观我们,其实也没必要——没那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这样做。
收集、采录了那么多歌谣和乐器,每首歌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有不同的意义,有没有哪首最为特别?哪种乐器最让你们动容?
乐器上印象最深的肯定是彝族月琴。它是一个高频段的弹拨乐器,从中亚传到内地,明末清初才传到彝区,这么两三百年里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整个世界的音乐里都少有,单独它一个乐器弹奏,一点儿不显单调。
我们不是有一首《哭嫁歌》嘛?采集这首歌的地方,几位彝族妇女唱歌的状态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她们就是最民间的彝族人,没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自己甚至有可能都不觉得在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音乐,这状态太动人了。
我比较喜欢《家支》里的乐器,是彝族的咬笛叫克西举尔,我觉得它是最能代表凉山彝族气质的乐器——深沉,神秘。月琴和大三弦比较贴合云南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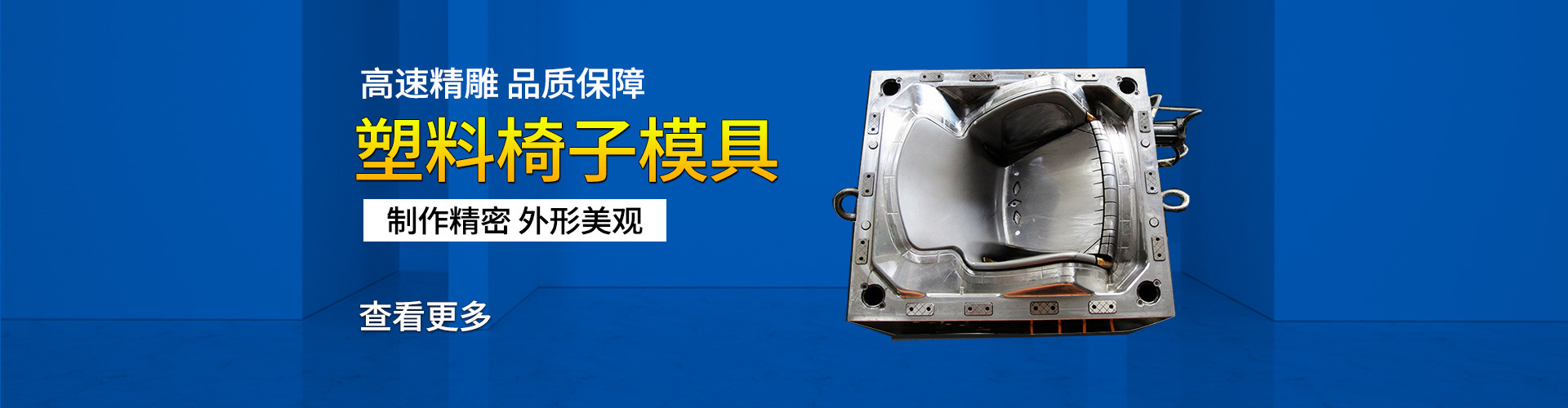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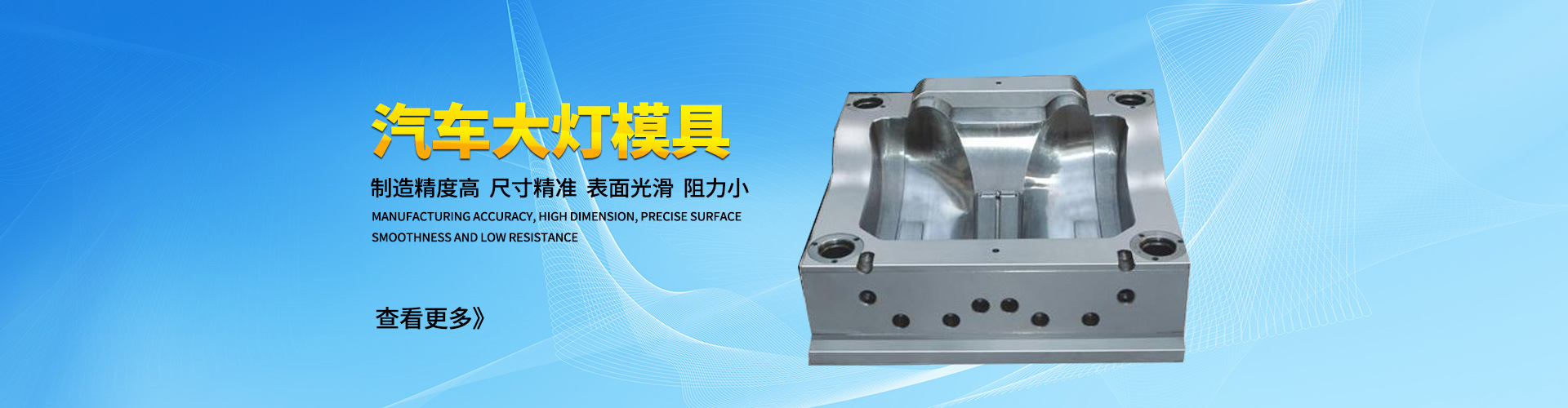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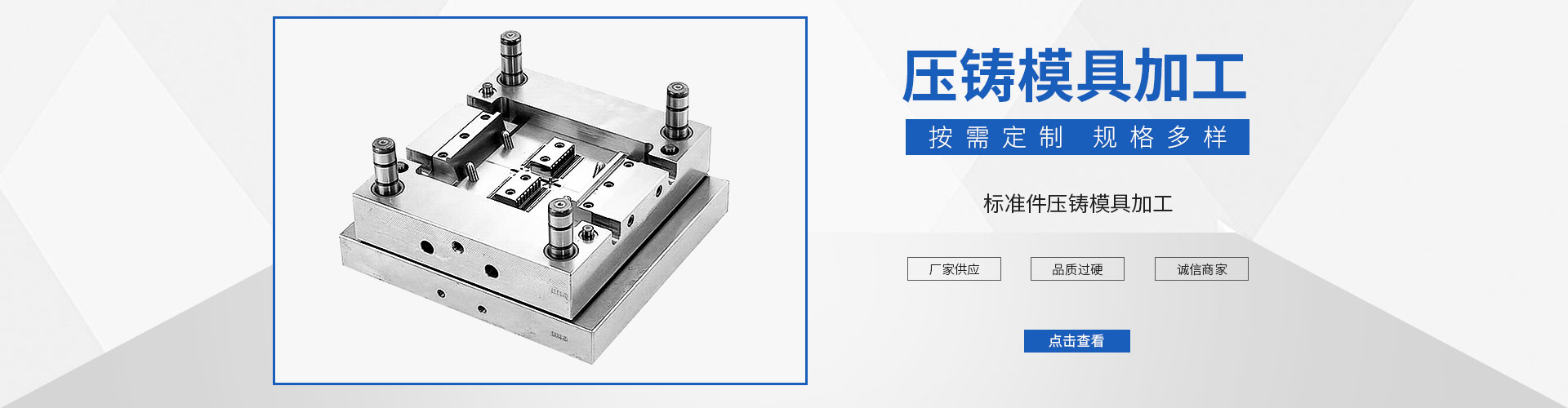
 更新时间:2024-02-24 21:18:20 来源:
更新时间:2024-02-24 21:18:20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