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海拔近3000米的云南哀牢山高寒山区,一个传统关闭的彝族山寨。村寨里家家户户都有火塘,人们用火取暖,用火烧饭,用火温暖情感。火塘里的火一年四季不平息,温暖着彝家人的日子,传承着彝族员的家风。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经常坐在火塘边,叼着长烟锅,沉着地吸着烟,不时地拨弄一下火塘里的柴禾,让火烧得更均匀。若爷爷不讲那段战火纷飞的年月,谁也幻想不到这个一般的彝族白叟从前为共和国短兵相接,扛枪八年的兵士。他讲那些他经历过的战役喝过的壮行酒,讲战友在身边倒下,讲歼灭敌人时的光辉。故事触目惊心,可爷爷讲起来很平缓,就像安静的深山日子。故事讲完又讲,柴烧完又添。爷爷的故事温暖了我整个幼年。
在我的家园,每一家盖好新房,首先要砌好火塘。搬新家,最要紧的便是转移火种。有人就得有火,有火才有家的温暖,有家的温暖才有好的家风,这是家园撒播的质朴日子道理。在我10岁那年,我父母亲咬着牙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搬迁的那天,我换上新衣裳,身披大红缎子,承担起转移火种的重担。那一天,村寨里的老毕摩念起陈旧的祭火经,把老房子火塘里的火炭分出一部分,放在一个簇新的火盆里。我捧着火种,从老房子走向新房子,把火从老家搬到新家。我走在最前面,爷爷和村寨里的白叟唱着彝族陈旧的祭火歌调跟在死后。一路走,一路唱,一向唱到新房子里的火塘里。
从老房子的火塘,到新房子的火塘,一个火塘繁殖为两个火塘。一个家庭,从此就变成两个家庭。火分得越多,越标志一个家庭的兴隆。让子女有自己的一个火塘是每一个彝家汉子的职责和责任,也是彝族员代代相传的家风。所以那一天也是我爷爷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彝族男人、一位父亲,总算完成了他的任务,把薪火传给了子女,让他们开端新的日子。
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咱们家人人都想从戎,有一种深沉的武士情结。我父辈五兄弟轮番上阵去参与征兵,但唯有我三叔走运入伍。叔叔先从戎,后来又提干,成了我爷爷最自豪的儿子,也成了我的标杆。我三叔每次省亲回家,总是先到火塘边。一家人围着火塘听他讲外面的国际。我也是在火塘边,听三叔讲起部队的现代化,讲和平时期戎行加快速度进行开展的改变。若说爷爷讲从戎交兵的故事,像一粒火种耕种在我的心里,那么三叔的故事则在我的心里添了一把火,让我愈加神往部队的日子。
山里的孩子,肄业困难。我从小学四年级就要去相隔十公里的外村肄业,初中到离家几十公里的镇上读,高中到远离家园几百公里的州城,上大学则在家园千里之外的省会。每一次前进,都有坐在火塘边爷爷温暖而深切的目光,都有我三叔千辛万苦的教育和赞助,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家风。大学毕业,我沿着爷爷和三叔走过的路途,参军入伍,成为武警边防部队的一名警官。第一次省亲回家,回到温暖的火塘,坐在爷爷的身边,一家人围着火塘,也把我围在中心,问这问那。
看着火塘里焚烧的火苗,我总算理解,这火塘,是咱们彝家人家风的传承,是咱们彝族员日子的寄予。没有火塘,咱们的祖辈就无法在瘠薄的高寒山区生计,就无法繁殖一代又一代后代。没有火塘,也就没有咱们三代武士的传承与期望。火塘,是咱们三代武士无法舍弃的挂念。 (毕仕举/武警红河州边防支队司令部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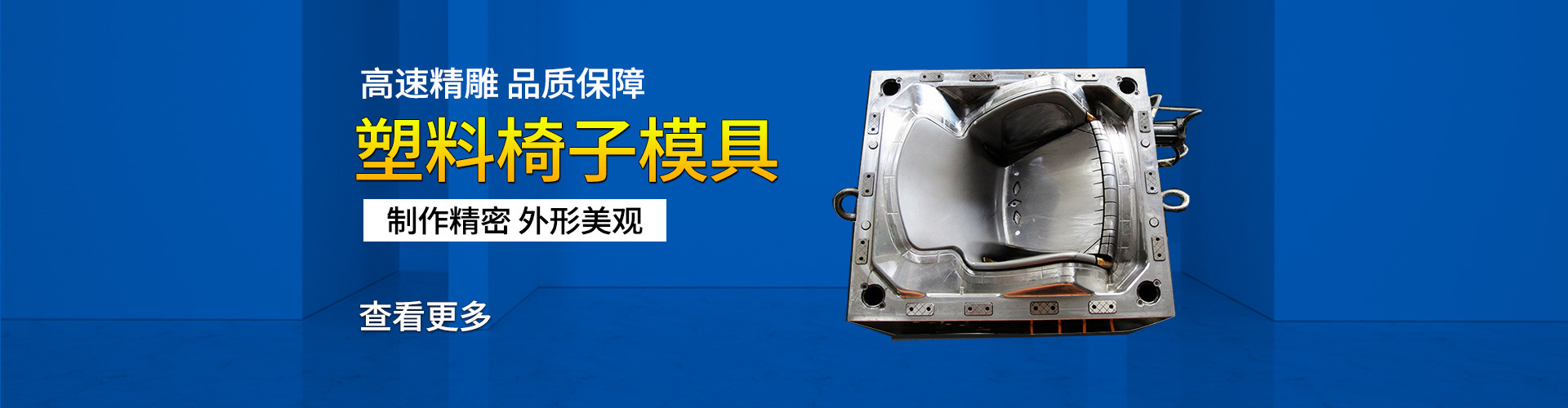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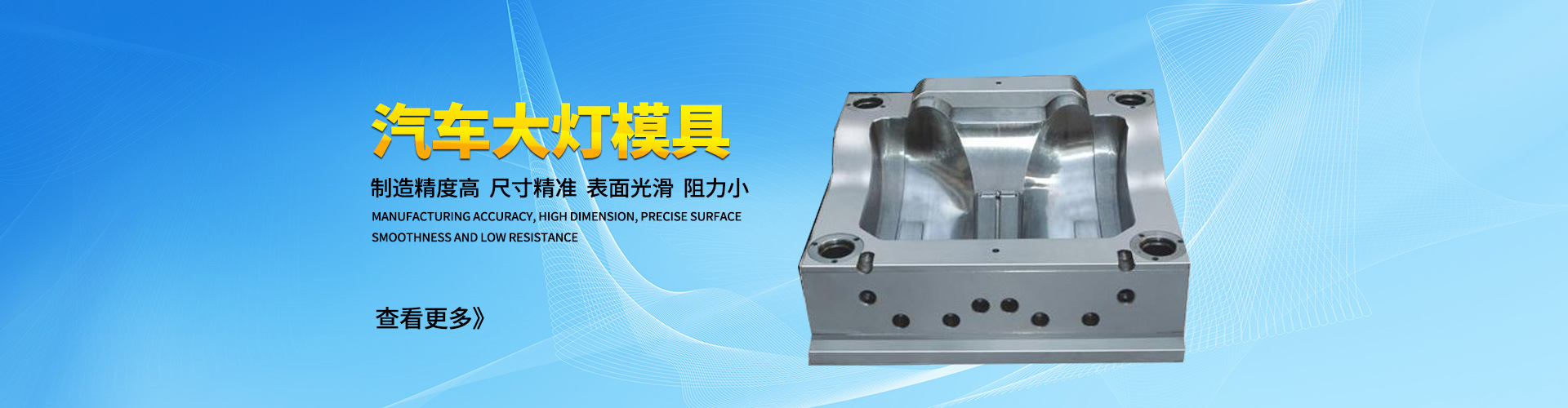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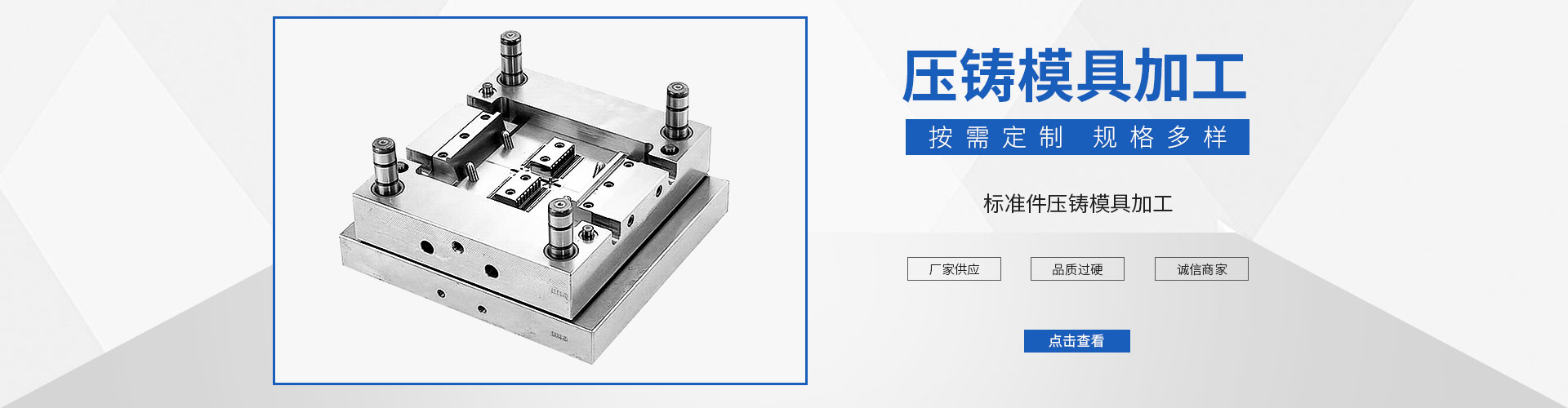
 更新时间:2023-12-13 13:18:08 来源:
更新时间:2023-12-13 13:18:08 来源: